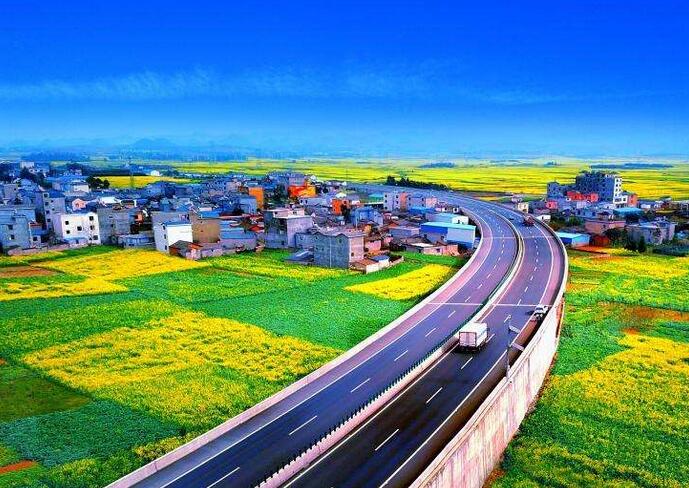【導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世界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十四五”期間,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突破65%。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越來越多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作為我國發展和治理基本單元的縣,成為這一進程的主要載體。但是,在縣域城鎮化突飛猛進的同時,“房地產化”現象卻愈發明顯。
“房地產化”是指城鎮化的推進過度依賴于房地產業,將房地產業作為推動人口進城與城市空間擴張的主要手段,它根本上反映的是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環節,以及以此為依托的人口聚集與公共服務完善。
作者通過對東部和中西部縣城的房地產與公共服務調查發現,當前縣域城鎮化已普遍陷入“房地產化”誤區,并呈現出房地產價格畸高、超越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聚集能力的典型特征。作者指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縣級政府將行政拆遷與公共服務捆綁,推動土地增值-融資貸款-高額財政支出循環,進而造就危險的“繁榮”。作者通過對“城市型”縣城和“鄉村型”縣城的分析,提出不同城市間要分工合作,不能籠統采用以房地產為中心的透支性發展模式。最后,作者強調縣域的城鎮化應盡快擺脫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依賴,找準自身定位,立足于城市自身特性,回歸合理的發展道路。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原題為《縣域發展何以陷入“房地產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明確了縣域城鎮化的重要地位。它對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意義重大,是中國城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當前不少地區的縣城建設正在陷入“房地產化”的困境,看似欣欣向榮的縣域城鎮化實則高度依賴盈利性房地產的驅動。這嚴重偏離了國家城鎮化的戰略目標,且已經產生了較多負面效應,蘊含著一系列的社會風險。
縣城房價畸高與被“房地產化”的縣域城鎮化
房地產業的發展與城鎮化的推進相伴而生,是城鎮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不過,由于房地產業能夠在短期內增加城市建設的資本投入,推動土地大規模的資本化,帶來可觀的利益增量與城鎮空間的擴張效果,這就使它容易被過度發展,引發城鎮化進程被“房地產化”的突出問題。“房地產化”是指城鎮化的推進過度依賴于房地產業,將房地產業擴張作為推動人口進城與城市空間擴張的主要手段,它根本上反映的是城鎮化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環節,以及以此為依托的人口聚集與公共服務完善。通常來說,陷入“房地產化”的城鎮化會在短期內引發房價猛烈攀升,出現地產泡沫化的問題,即高額房價難以匹配城鎮化所要求的工業化水平、人口聚集程度以及公共服務能力。從實踐來看,近年來,無論是在東部發達地區的縣城,還是在中西部地區的普通農業縣,各地縣域城鎮化的推進都普遍伴隨著房地產業的興盛與房價的畸高,縣域城鎮化陷入“房地產化”的趨向日益凸顯。
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共計90個縣(市、區),根據2022年8月的數據,這90個縣(市、區)房價均價超過2萬元每平方米的有29個,超過1萬元每平方米的多達85個,僅有5個區縣房價均價低于1萬元每平方米,但也超過了8000元每平方米。浙江屬于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程度較高,但縣城的畸高房價仍然與縣域經濟的發展水平不相匹配。2021年,浙江省共有25個縣(市、區)的GDP超過1000億元,這25個縣(市、區)大多屬于核心城市的轄區或經濟發達的縣級市,剩余65個縣(市、區)GDP均低于1000億元,20個縣(市、區)GDP仍低于300億元。這表明,大量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人口密集度不高的縣城也維持了高額房價。例如,衢州位于浙江省的山區地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其下轄的1區5縣中僅核心城區屬于人口流入地,其余5縣的常住人口均少于戶籍人口,但六地的房價均價均超過1萬元每平方米。價格最低的常山縣2021年的GDP僅為187.58億元,房價均價仍高達10693元每平方米。顯然,縣城房價攀升事實上并不是依托于縣域經濟人口總量的提升。
與此同時,大量中西部地區的縣域城鎮化也普遍陷入“房地產化”的窠臼,且呈現出更為嚴重的房價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聚集度、公共服務質量失衡的狀態。以地處中部的湖北省為例,該省共有103個縣級區劃,除去39個市轄區(含3個直管市)外,共有縣級城鎮64個,根據2022年4月的統計數據,64個縣級城鎮中,房價均價超過5000元每平方米的縣城達到24個,超過4000元每平方米的縣城有47個,分別占縣城總數的37.5%與73.4%。相比東部發達地區,中西部縣城的房價明顯較低,但這些縣城大多屬于以農業經濟為主的人口流出縣,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水平也相對落后,它們大多依托縣域城鎮化實現了房價大幅度上漲,不少縣城的房價甚至開始接近地市級城市的房價。例如,湖北咸寧市共有1區5縣,2022年其核心市區咸安區的房價均價為4502元每平方米,5縣中除赤壁市經濟較為發達外,其余4縣的經濟能力明顯弱于市區,且面臨著人口大規模外流的問題;但近年來,這幾個縣城的房價卻不斷攀升:通城縣2021年的GDP總量僅為191.04億元,不足市區的二分之一,全縣52.7萬總人口中有12萬的外出打工人口,但2022年,該縣房價卻攀升到4239元每平方米,接近市區房價。可以說,持續落后的縣域經濟、大規模外流的人口與不斷高漲的房價,已經構成了很多中西部地區縣域城鎮化的突出特點,其經濟、人口與房價的高度不平衡比東部縣城表現得更為突出。
這深刻表明,當前縣域城鎮化已經普遍陷入了“房地產化”的發展誤區,并呈現出房地產價格畸高,超越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聚集能力的典型特征。
依托房地產推動的縣域城鎮化模式
依托房地產推動的縣域城鎮化模式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其核心是在縣域人口與產業狀況未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通過行政手段制造商品房需求、推高房地產市場價格,并利用房地產的發展造成人口進城購房、城市空間擴張的短期效應。這一模式包含三重基本操作。
第一,利用行政手段改變縣城商品房市場的供求關系,人為制造大量購房需求,從而推動商品房市場蓬勃發展,實現房價快速增長。在地方政府積極干預前,絕大部分縣城的房價都與本地的人口、產業狀況相契合,商品房需求相對穩定,一般只有在縣城擁有穩定就業或有購買投資能力的群體,才會在縣城購房。中西部地區的縣城由于缺少工業產業、人口大量外流,其商品房更是長期處于較低的價格水平。正是為了突破房地產市場的穩定運行狀態,撬動更大規模的土地非農化與土地增值收益,在縣域城鎮化過程中,縣級政府遂有著強烈推動房地產業發展的訴求。從具體實踐來看,縣級政府普遍依托行政權力,積極利用棚戶區改造、舊城改造等政策,展開大規模的“拆遷運動”。“拆遷運動”起到了兩重效果:一是借助政策撬動大規模財政資金。無論是“棚改”還是“舊改”都附著了較大規模的項目資金與優惠貸款政策,能夠用于增加地方可支配的財力,這對財政資金緊缺的中西部縣級政府尤為重要。二是以拆遷制造非市場性的商品房需求。為了將拆遷戶的住房需求引入商品房市場,縣級政府一般都會積極推動貨幣化補償模式,并以優惠政策引導拆遷戶將補償款轉換為商品房。
由此,公共財政資金就能以拆遷補償款的形式涌入房市產市場,在短期內制造大規模購房需求,引發房價激增。以筆者調研的中部T縣為例,該縣在2016~2019年間,借助縣域城鎮化申請了13個“棚改”項目,涉及拆遷6879戶,并獲得了10億元左右的融資貸款。T縣利用這些融資貸款,以增加各類補貼的形式,提高拆遷補償標準,使該縣的拆遷補償價格略高于商品房價格,引導拆遷戶購買商品房。棚戶區改造的第二年,該縣的房價均價就從原來的每平方米2500元增長到3500元,2019年房價均價已經高達4038元每平方米。
第二,將房地產市場與民生公共資源的分配相掛鉤,制造鄉村人口進城買房的動力,從而造成人口向縣城聚集的可觀現象,并進一步拉高房價。中西部縣城的工業化水平較低、就業機會有限,城區常住人口有限,鄉村是人口的主要聚集地;東部縣城的常住人口較多,但基于較高的城鄉一體化水平,絕大部分本地人口也仍然愿意在鄉村居住。為了撬動人口進城,縣級政府普遍通過調控縣域民生公共資源的配置,影響農民的購房與居住決策。一般采取的手段是,在縣城集聚優質教育資源,興建遠超鄉村建設標準的高質量學校,大幅度增加縣城學位、抽調優質教師資源,拉大縣域內部城鄉教育質量的差異;同時,嚴格規定只有在城區擁有戶口或商品房產權的家庭才可以獲得城區的入學資格,從而影響教育資源配置。
由此,盈利性的房地產就與民生性的公共服務緊密捆綁,是否擁有城區的商品房產權成為享受縣城優質教育資源的基礎條件。縣級政府也因此得以“撥動”城鄉社會的敏感神經,激發鄉村人口進城,實現增加縣城常住人口、維系房價高位運行的目的。以中部省份H縣為例,該縣常住人口90.19萬人,外出打工人口22.9萬。為了推動人口進城,2016年,該縣投入13億元興建高標準教育新城,增加了13600個學位(涵蓋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且每年遴選優質鄉村教師到新學校任教。這使該縣的城鄉教育差距在短期內迅速拉大,為了讓孩子在縣城入學,農民不得不購買相應的商品房。該縣的房價很快實現了飛漲,2016年前該縣房價僅為2600元每平方米,且很少有人問津,而2021年就已經飆升到5000元每平方米。
第三,隨著商品房價格激增,縣級政府得以撬動大規模的土地財政收入與融資性貸款,維系縣城的高規格建設,從而實現縣城在空間上的快速城鎮化,并持續維系高房價。通過行政化拆遷與公共服務“捆綁”,縣城房價快速攀升并轉換為縣城土地價值與需求規模的增長,從而增加了縣級的土地財政收入與融資性貸款。依托土地融資產生的金融乘數效應,縣一級可支配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通常十分可觀,這些財政收入能夠持續投入到縣城建設中,維系土地城鎮化的快速展開。大量縣城正是以此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建設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一些中西部縣城也出現了越來越多“豪華”的城市設施與景觀。不過,縣級政府的公共投入仍然有較強的指向。為了維持高額房價,城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服務主要集聚在新建商品房周邊,作為房地產的配套設施。這在財政資源緊缺的中西部縣城表現得尤為明顯,很多縣城在城鎮化過程中都形成舊城區與新城區的顯著區分,新城區房地產密集,周邊基礎設施較好、較新,而人口與商業相對聚集的舊城區則基礎設施落后,很難得到政府的投資與建設。
由此,一方面,通過將行政拆遷與公共服務“捆綁”,縣級政府在短期內制造了大規模的購房需求,大量公共資源與社會資源被動員進房地產市場,推動房地產市場的興盛與畸高的房價;另一方面,房價高位運行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與融資性貸款,又進一步維系了政府制造購房需求所需的高額財政支出。兩者的疊加與循環,使縣城可以不依托經濟與人口增長,只通過迫使農民進城購房,就能實現縣城空間的快速擴張,縣域城鎮化就此呈現出“繁榮”圖景。然而,這一模式的城鎮化卻嚴重背離了國家的城鎮化目標,蘊含著巨大的風險。


 智庫動態 NEWS
智庫動態 NEWS